发布日期:2025-07-17 09:58 点击次数:18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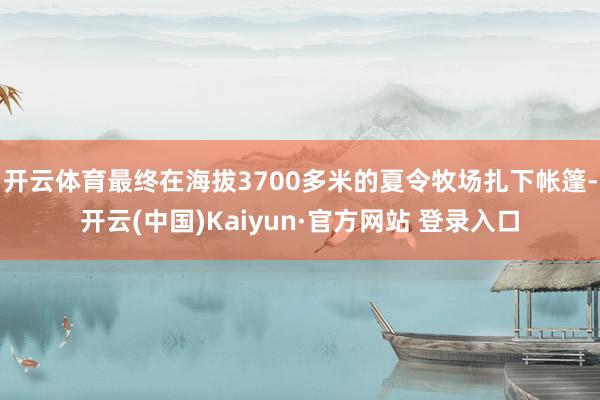
新华社西宁6月28日电(记者张龙、皆芷玥)六月盛夏,祁连山深处仍是山风料峭。朝晨,61岁的牧民万卓紧了紧藏袍,拎起一壶奶茶,翻身上马,一声吆喝,引着三百余只羊爬上山坡。坡顶,他的外甥先巴尖措落寞不异装饰,站在曙光中,赶着牛群慢步前行。
 6月25日朝晨,先巴尖措走在转场路上。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
6月25日朝晨,先巴尖措走在转场路上。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每年此时,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牧民们转场的日子。数千户牧民赶着牛羊,不息告别冬牧场,跋涉数百公里,几经休整,最终在海拔3700多米的夏令牧场扎下帐篷,开启夏牧生活。待到八月中旬天气转凉,他们将再次踏上转场路,带着羊群回到冬牧场上的家。
万卓的家,就在祁连县默勒镇才什土村。算起来,这大致是他第五十次走上转场的路。虽年逾花甲,但万卓依旧乐在其中,每年夏天重返草原,他总感到分外赋闲。
天色微亮便起程,行进了三十公里,杰出七八个垭口,目下豁然轩敞,一条直接的公路通向辽阔。
 6月25日朝晨,在转场路上的万卓。新华社记者 皆芷玥 摄
6月25日朝晨,在转场路上的万卓。新华社记者 皆芷玥 摄万卓呼唤先巴尖措,在铁丝网上拴了马,又将牛羊驱到路边。高原正午的太阳后堂堂,把草原照得发亮,万卓和外甥起步当车,倒上奶茶,掀开一袋子馍馍,这等于转场路上的午饭。
东说念主吃饭,牛羊也在不辽阔吃草。万卓盯着羊群,一只羊羔步态哆哆嗦嗦。“这只走不动了,需要坐车了。”万卓打电话叫来了东床,防卫翼翼地把羊羔抱上车辆,此后东床扎西尖木措开着车,转运前行。
暑往寒来,这片地皮上的牧民,恒久坚守着随季轮牧的传统,但千年未始断交的山歌如今也在发生新变化。“连年来,跟着基础尺度和牧民们生活的改善,机械化的转场形势迟缓升迁,已往依靠畜力举家搬迁的场景已难觅行踪。”默勒镇镇长房世荣说。
下昼五点,尽管昭节高照,但万卓依旧决定安营,“一天弗成走太多,否则羊群太累,淋了雨撑不外去。”半世纪的牧业生存让他警戒丰富。
兜开篷布,撑起架子,万卓抡石将铆钉钉入土中,一座浅易帐篷便立在了田园。日影渐斜,暮色初合,先巴尖措支起便携炉具熬茶作念饭,蓝色火苗舔舐着锅底。帐外,牛羊安卧,四野渐寂。
 6月25昼夜间,先巴尖措在帐篷内休息。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
6月25昼夜间,先巴尖措在帐篷内休息。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未来朝晨,万卓与外甥又驱着牛羊向夏牧场行进,直到正午技术终于抵达。高原天气善变,抵达时,疾风骤雨倏但是至,不顷刻间又是昭节高照。牧场上,一座浅易板房为舅甥二东说念主对抗了风雨。
“当今夏牧场上也建了板房,比帐篷更暖和,很多大件的物品也无谓搬来搬去了。”万卓说。
板房内,沙发、碗柜、火炉一应俱全。走了两天,万卓微微有些累,倚在沙发上盯着窗外。雨过天晴,牧草上还挂着雨珠,“本年雨水好,草长得好,牛羊能吃个饱饭了”。
将来40余天,与万卓一样的数千户牧民将在草原深处放牧开云体育,对绵延的祁连山而言,这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的移动,更是草原治疗孳生、生态归附的枢纽技术。